杨振宁到底有多牛?杨振宁中国的“爱因斯坦“”
作者:Sandy 人气: 222021年10月1日,杨振宁先生将迎来农历100周岁生日,学术界纷纷推出活动或文集祝贺杨先生百岁诞辰(杨振宁先生护照上的生日为9月22日,但据李炳安、邓越凡两位教授考证,杨振宁先生生日为10月1日。[1]恰巧与国庆、杨振宁发表获诺贝尔奖之论文的日子相同。今日《知识分子》和《赛先生》文章各取一说)。
《赛先生》自8月起陆续刊发系列重温杨振宁先生重要贡献的经典文章。即日起将与《知识分子》联合推出 “百年风华杨振宁” 系列文章。邀请朱邦芬、潘建伟、施一公、饶毅等科学家及杨先生学生为杨先生百岁诞辰送上祝福。

杨振宁先生对中国科学的影响,不仅在于他自身取得的卓越成就,更在于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是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同样能够做出顶尖的科学发现,激励着众多年轻学者投身于科学探索之中。一路走来,我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也一直得到杨先生的有益指引。
潘建伟:三十年前初见杨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1992年6月。当时,中国科大为了庆祝杨先生70岁生日,举办了非线性科学与理论物理学术报告会。我当时刚刚本科毕业,兴冲冲地一早就来到了会场,非常巧地正好坐在杨先生的身后。
那时候还没有PPT,参会的谢希德、葛庭燧等老先生都是手拿胶片在幻灯机上边写边讲,将熟记于胸的复杂原理娓娓道来,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生,确实是感受到大师精于治学的风范,当然也听不太懂。我还清晰地记得杨先生当时讲过的一段话:对于你们年轻人来说,听这样的报告不一定马上就能有所收获,但也许在将来某个时刻,你会发现你以前所听到的会影响你的一生。
实事求是地讲,当年的那场学术报告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过于深奥,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杨先生的这句话;而没过几年,这句话就得到了应验。1995年,我参加了葛墨林先生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当时我在科大读研,学习的是量子物理基础理论。我趁着理论物理研讨的机会,希望可以与前辈们交流一下我硕士论文的内容,做了关于量子芝诺效应的报告。
在会议上,我了解到杨先生认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果然,后来激光冷却原子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BEC的发现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当年Eric Cornell、Wolfgang Ketterle、Carl Wieman刚刚实验实现BEC,杨先生就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它的重要性,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BEC这一概念。南开大学的这次会议,对我后来科研道路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1996年我到奥地利留学,从此进入了量子信息这一新兴领域。最初我们开展的是量子光学实验,但随着理论和实验技术的发展,由BEC而兴起的超冷原子量子调控对于实现可扩展的量子模拟和计算的重要价值愈发显现。因此,我在从事光量子信息研究的初期,就拟定了超冷原子量子模拟和量子计算这一长远目标。时至今日,这个方向一直是我们实验室工作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2001年,我开始在中国科大组建实验室,在国内开展光量子信息研究工作。正是为了超冷原子量子调控的梦想,在国内发展光量子信息技术的同时,2003年起,我又在德国洪堡基金会索菲亚奖(Sofja Kovalevskaja Prize)、欧盟玛丽·居里杰出研究奖(Marie Curie Excellence Award)以及德国研究协会(DFG)Emmy Noether基金的支持下,在德国开展合作研究,积累相关的技术。
到了2004年,我们在国内的团队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当年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五光子纠缠,我国的量子信息实验研究终于走在了国际前列。2005年3月,朱邦芬老师告诉我,杨先生对五光子纠缠的工作很感兴趣,问我能否向杨先生介绍一下量子信息技术。
潘建伟与杨振宁的电梯趣事
那是我第一次和杨先生面对面地交流。我们在杨先生的办公室交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杨先生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末了还意犹未尽地邀请我到家里吃饭。通过与杨先生的交谈,我感受到他虽然已是高龄,但思路却非常的清晰,对于新鲜事物,比如我所从事的量子信息研究,更是如同孩童般充满好奇,这也许就是杨先生之所以成为物理学大师的根源。
杨先生对我们在光量子信息方面的工作非常认可,并且意味深长地讲道“激光有无限的future”。在杨先生家里,我看到客厅的名字就叫“归根居”,非常感动。临行前,杨先生赠送给我一本《杨振宁文集》,并且鼓励我尽早全时回国工作。
2008年,我在国外的技术积累已经比较充分的时候,全时回到中国科大工作。回国所开展的工作,除了在光量子信息处理方面继续发展外,我一直铭记着当年杨先生对超冷原子的判断。同时也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超冷原子的量子计算与模拟已然成为国际上最前沿的领域之一。
很多科学家回国是受杨先生感召
2009年,杨先生在接受《知识通讯评论》的采访时讲道:“这新领域叫做‘冷原子’研究,现在是一个最红的领域……这个领域还要高速发展,在50年代可以说是理论走在前面,现在则是实验带着理论走……”尽管当时国内在超冷原子量子调控方面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但杨先生的话无疑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深入这一领域的决心。
2010年开始,我们着手搭建超冷原子实验平台。经过数年的学习和积累,到了2016年终于有了比较好的进展,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利用中性原子实现了二维自旋轨道耦合的人工合成。此后又不断地实现新的进展,到目前,我们已经成为超冷原子量子模拟与量子计算方面走在国际前列的研究团队之一。因此,尽管我与杨先生并未从事同一方向的研究,但杨先生对物理学前沿的敏锐判断以及对年轻人的鼓励,一直是我们前进的指引。
杨先生对我的帮助,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方面。自我回国开展光量子信息实验研究时,其实就已经与我在奥地利留学时的老师Anton Zeilinger教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后来甚至和他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对我们的国际合作带来了一些困扰。
潘建伟:杨先生曾帮忙斡旋家事
杨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地帮我协调,专门邀请Zeilinger教授到清华来访问,借此机会和我还有Zeilinger教授一起进行了沟通,促使我们团队后来和奥地利科学院基于“墨子号”卫星成功开展洲际量子通信的合作研究。直到现在我们和Zeilinger教授团队还时常有合作。因此,在大多数人看来,杨先生是受众人崇敬的科学大师,但对我而言则更像是一位充满智慧且关爱学生的师长。
与杨先生的交往中,还不时出现一些趣事。我还记得在2005年第一次与杨先生交谈时,他告诉我获得了当年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后来我到新疆去参加颁奖典礼,正好在电梯里遇见了杨先生。我很激动地向他问好,杨先生却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回答是中国科大的。杨先生说科大有一个叫潘建伟的工作不错,这回获奖了。我只得直言我就是潘建伟,杨先生听后哈哈一笑,说:“抱歉,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子了。”
后来又与杨先生见过几回面,他仍然没有记住,直到见面的次数多了,才终于记得我的样子。其实这并不是由于杨先生年纪大了,我们团队的很多年轻教授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一个人的工作记得很清楚,却往往记不清他的长相,这应该是我们都专注于学问本身使然。
还有一次偶然的事件让我印象深刻。2016年杨先生在北大出席求是颁奖典礼时不慎跌倒。杨先生当时已是九旬高龄,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揪心,杨先生却像一个孩子似的笑着对我说,潘建伟啊,我刚才摔了一跤!无论是“脸盲”还是“老顽童”,其实都是体现了一个学者醉心于学术的纯净的灵魂;而这种纯净的灵魂,正是产生大师的心灵土壤。
杨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告诉过我一些他过去的经历,例如,1945年他出国留学的时候,在去往美国的船上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感叹道世上竟然有如此美味的食物。杨先生甚至还说,直到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吃饱了。从这些略带辛酸的往事,可以感受到杨先生他们那一辈科学家,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求学的不易,而这份对科学真理的向往和执着,最终带来了中国今天的科技繁荣。

2019年,随着“墨子号”量子卫星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们荣幸地将“墨子号”载荷样机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杨先生出席了捐赠仪式。在捐赠仪式上,杨先生感慨道:“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着中国‘天亮’,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是的,杨先生所经历的这100年,恰是中国的科学研究从拓荒到腾飞的100年。杨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执着求真、关怀后进的精神,将一直激励我辈勇担科技创新的时代重任,这也是我们能献给杨先生百年华诞最好的贺礼!
[1]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杨振宁先生主页上,刊载了由肯塔基大学荣休教授李炳安(曾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工作)、美国纽约州立石溪大学教授邓越凡在1992年为杨振宁先生撰写的小传,小传一开头即明确写道,杨先生的生日应为1922年10月1日,但在他1945年所用护照之上出生日期被错误地记录为1922年9月22日,因此杨先生之后所有的正式文档中均使用9月22日作为其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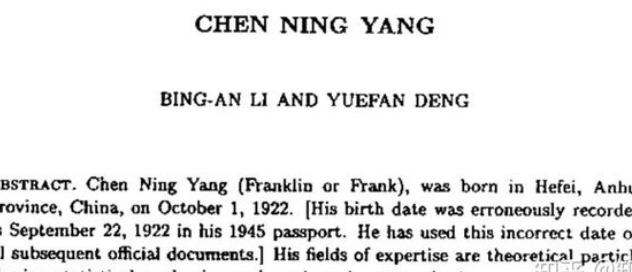
另据2021年2月出版的由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杨建邺所著的《杨振宁传》中,杨振宁先生的生日明确为1922年10月1日
加载全部内容